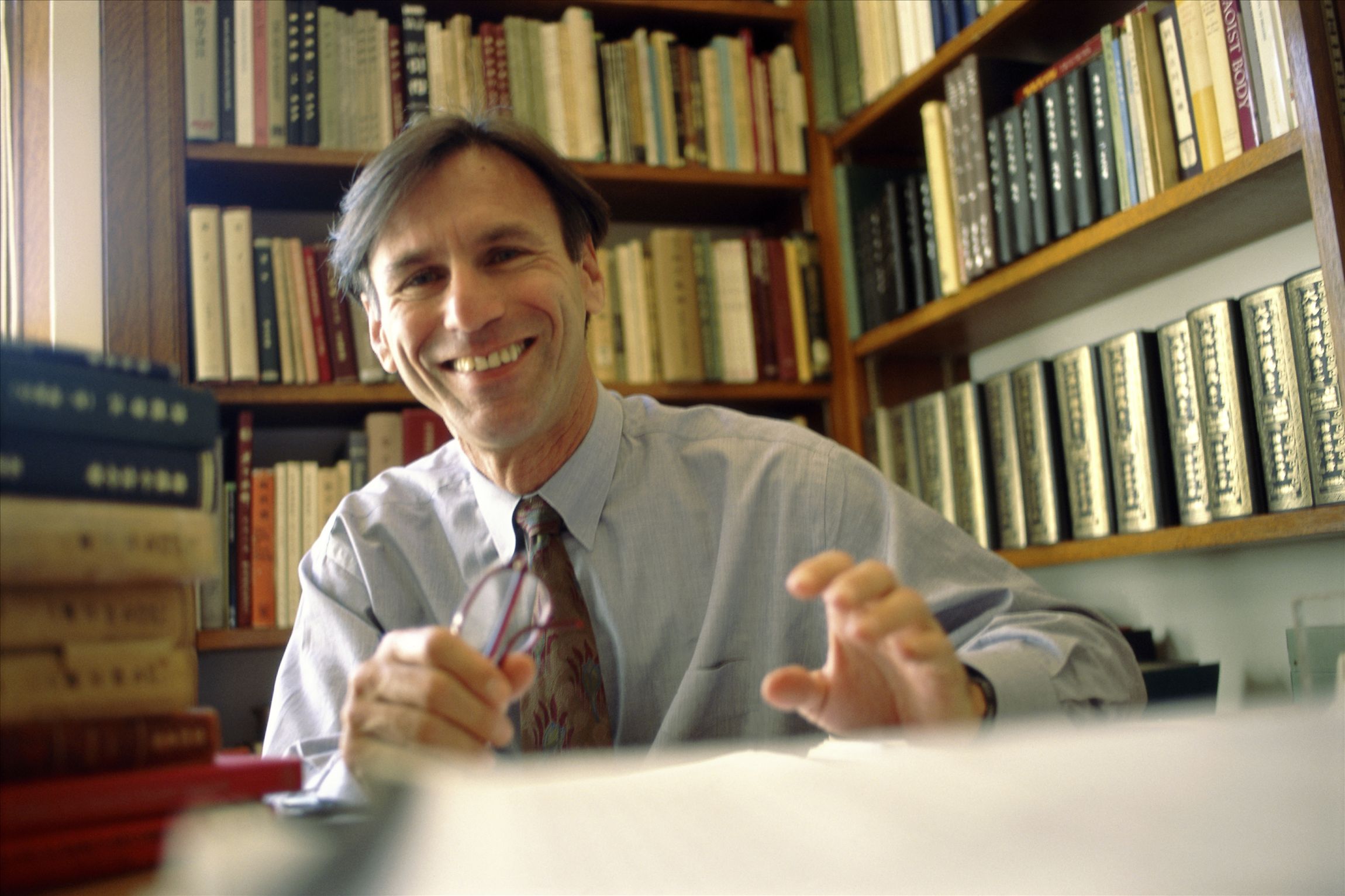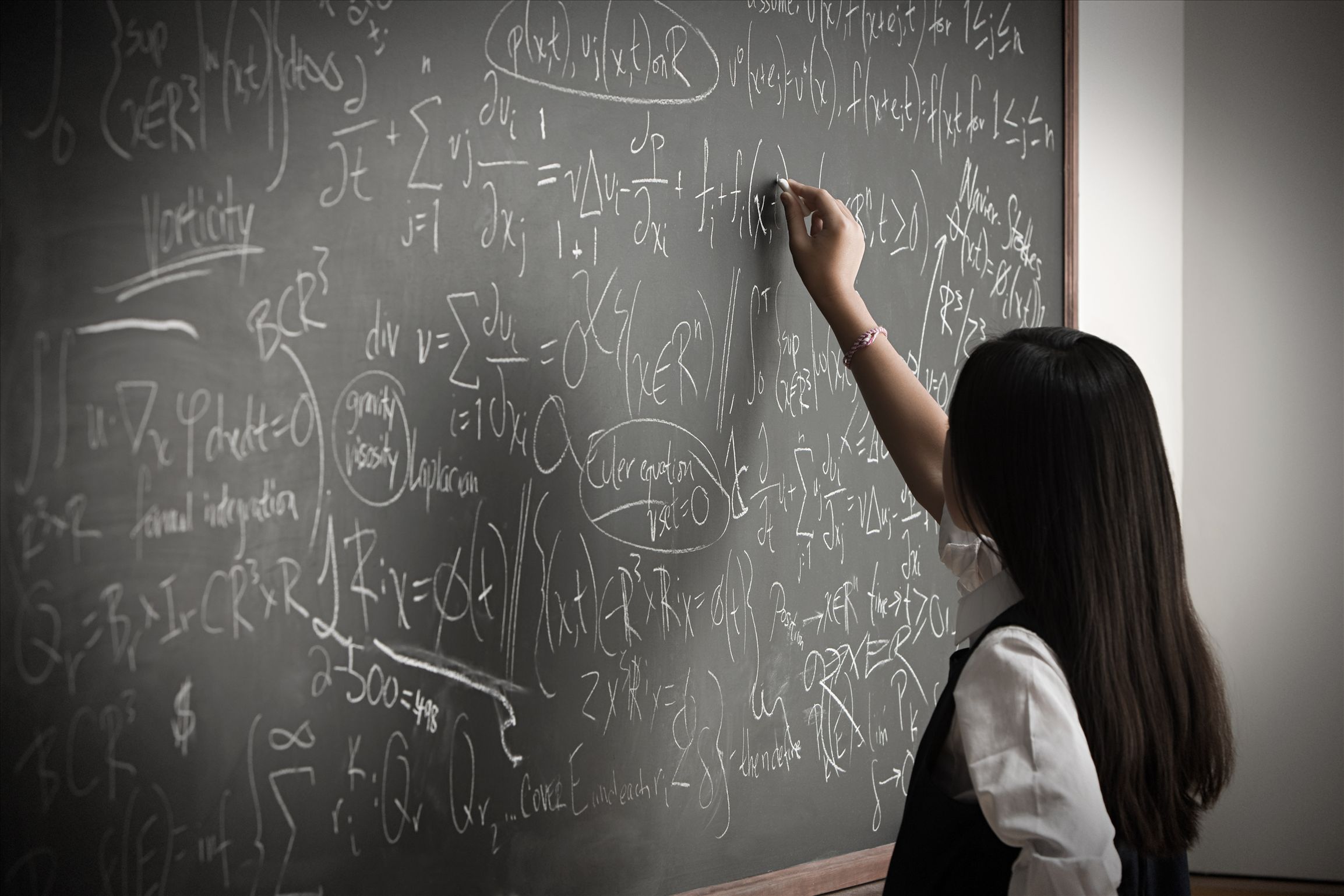略論行政局的組織與功能
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從來就是政制上最重要的課題,因它基本是奠定了政制的模式及實際政治的運作,從而影響了政治決策的所屬及效應,也影響了政治權力的分配。 這個本應給予高度關注的問題,惜乎在制定基本法之時,卻被大多數人所忽視,因為那時大家所注意的,儘是”直選”、”間選”,及有多少個直選議席等,亦即是多數人只關心”霸橙仔”的問題。 果然,在基本法頒佈後的後過渡期,由於政制需要發展並要與基本法銜接,加上實行直選以後所產生的政治形勢上的變化,使行政局的組織,與及誰可以,誰應該進入行政局,逐漸被大家所關注,甚而成為了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 由於這個問題,需要很迫切地處理,故相信彭定康總督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將無可避免地要觸及這個問題,本文刊出之日,彭督經已在立法局宣讀其施政報告,也已分別在大會堂及沙田大會堂公開簽覆市民的質詢,本文似已明日黃花,但有關本港應如何處理行政局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仍是極具討論價值。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過去一百多年來,英國在香港實施的是殖民地的統治,故其政府組織,完全是殖民地政府的模式,港督作為英皇的代表,根據”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在港組織政府及種種施政,進而成立由過去以迄現在模式的行政局及立法局,完全合乎殖民政府的邏輯及需要。儘管加入了直選成份的立法局,在實際政治的形勢上已起了根本的變化,但在憲政體制上,卻仍然沒有改變–仍然是港督的顧問。 明乎此,我們就不必在討論過去的香港政制問題時,以西方世界所通行的什么”總統制”、”內閣制”或”委員會制”來套入香港政制,因為殖民地就是殖民地,無所謂合理,無所謂邏輯,權力就是一切。 由於行政局議員及立法局議員,在過去都同屬港督顧問,分別就只是職責上的不同,而且全部是委任,則誰被任命,立法及行政是合一抑或分家,均不成問題。 但當中英聯合聲明公佈,香港回歸問題開始放在日程表之上以後,英國人便刻意要在香港推行民主化及代議政制,(那時英國或許不理解中方對”現有”政制一往情深,竟至於此,也不理解中英對”民主”一詞的闡釋竟有如此大的分別,更料不到任何由英方單方面推動的”民主”,都會被懷疑為英方的”陰謀”。因而在一九八六年的”代議政制錄皮書”中,開宗明議,就說要建立一個立根於香港,為香港人所接受的代議政制,同時亦提議未來的行政局,有一定的比例由立法局選出。 姑不論英人提出此一模式有無陰謀,但在邏輯上乃是絕不可行的。因香港立法局不是全面民選,港督也不是由立法局推選出來。則作為港督之”內閣”或”顧問”的行政局成員,若其中一些由立法局選出來而與港督意見相左時,如何處理?豈非面臨憲政危機或政潮?故所以在以後公佈的”白皮書”中,便不再提及實非偶然。 及至制定基本法之時,由於大多數人只關注立法局的組織及議員的產生方法,(這是理所當然的,由於政團的競逐,只能以此為對象),對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與及行政長官的權力,均未予足夠的重視;加以當時大多數人的心理,是惟恐未來有太大的改變,以致影響安定繁榮。故甚基本法中,絕大多數其實是將當時已有的,只不過是用文字加以明確化,其中行政局,即以後的行政會議,也大致如此。 問題在於九一直選以後,由於號稱”民主派”的港同盟囊括了大多數直選席位,他們覺得在實力上,在代表性上應有部份成員可以進入行政局,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不願接受”保密”及”集體負責”的守則。 這問題可複雜了,由於港同盟的要員,大多數也是”支聯會”的成員,而支聯會仍被中方定性為反對中國政府及支援反革命活動,中方萬萬不願支聯會成員進入港府決策的核心當中,港同盟成員五方面覺得自己的代表性被任命為行政局成員是理所當然的,否則,已具政黨性質的為聯資源中心成員,卻仍擔任行政局議員,豈不是極度不公平? 這實在是彭督上任後,在政制問題上最棘手的問題,此所以有此一說,有謂彭督將實行”兩局分家”的模式,但這一來又被港同盟所反對,認為這是有意排擠他們,向中方屈服,但另一方面港英卻難免又被懷疑是否又是另一種”陰謀”。 本來,理智一些來看,過去行政局的模式及其與立法局的關係,實在是不倫不類,只是由於過去兩局都全由港督委任,具可說俱無實權,則是否分家,完全無關宏旨,當立法局引入直選,並取消官守議員以後,在立法局中委任一些”心服”兼任行政局,俾政府議案能順利通,既有利溝通,又能發揮”護航”作用。只是形勢比人強,一方面是港同盟口口聲聲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委任議員督在未來肯定要大幅度減少,則分家應是最佳選擇。 況且為港督的”內閣”或 “顧問團”,無論其為顧問的角色抑或共同決策者,我們實難想像行政局成員既不”保密”,也不”集體負責”,試想,開完會後,各說各的,或在一些重大決策,在研究或醞釀之前,便各自先向自己的政團或選民諮詢,將會變成怎樣子? 這即在如何民主的國家,也屬不可能,除非是”聯合政府”,但香港會產生”聯合政府”的模式嗎? 所以依現有體制,不遵守”保密”及”集體負責制”者,便不應該成為行政局成員,要講話,要發揮監督政府的責任,應該在立法局而非行政局。 何況,依現有體制,行政局可以有無上尊榮與權威,也可以完全無足輕重,一切視乎總督怎樣看你,用你!他可以將一切決策權交給你,也可以另行成立什么”智囊團”,也可以在內閣中再有內閣,重大問題由自己與政治顧問布政司,甚或自己”攪掂”。 故聰明而有實力的政治人物,不必要求成為行政局議員。 行政立法局分家,行政局完全變回港督或行政長官的幕僚、智囊、或閣員,是最合邏輯的方式,因立法局及未來行政長官,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來源,沒有理由再”溝工亂”。 只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卻來了,因為:今日的政制必須與九七年後的互相銜接。任何政制不能不符合基本法,而基本法在制定之時,大家的內心,以各地方在實際的條文上,大都是按照當時的既有模式為藍本的,故若有任何改變,最多只能夠做些基本法內沒有明文禁止的;若與其規定有明顯抵觸,則絕不應該,也不可以。 同時,一切改變,除了因應港人的意願外,還須要中英雙方取得諒解、默契。任何爭論,都會對香港的安定繁榮,造成負面的影響,這誠我們所關注及殷切期望的。
Continue Reading